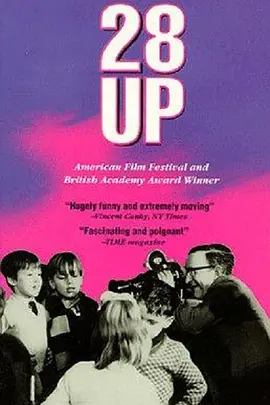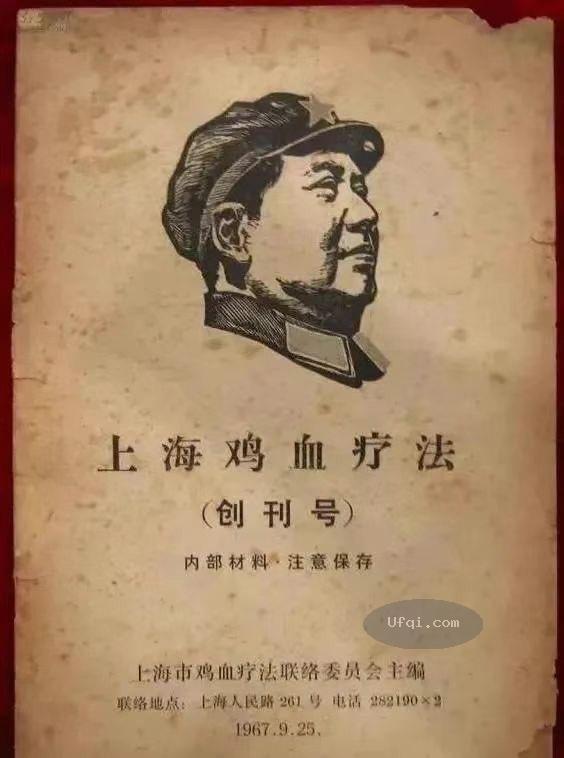2020-12-17 , 1429 , 104 , 169
写在前面:写前面几篇的时候,尽量去除了“我”的视角,想让文字看起来客观纯粹一些;现在题材将尽了,不得不回归我,我的生活、我的视角,有点唠家常的感觉,估计会有些唠叨磨叽。
村子里亲戚脉络极其广泛,同村的、邻村的,不论姓啥,捋吧捋吧总能论(土音lìn)上亲戚。男方女方两系交织、辈分相叠,家族大一点的,刚出生的孩子也能当爷爷。亲戚的称呼也特别多,又有父方母方之分,辈分之分,堂表之分,排序之分……
小时候害怕串门儿,怕碰到个亲戚不知道叫什么,比如每次去大姨家,总想不起来也捋不清楚,应该管她家儿子的岳父叫什么。
嗨,挺大个人,六亲不认!
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姑姨大爷叔叔和姨舅,婶子舅妈姑父姨夫,哥嫂弟妹,姐夫小舅子,妯娌连桥儿堂表兄弟……
汹涌的亲戚人潮,逢年过节,熙熙攘攘。人情来往嘛,都是村里的传承,父母常说要走动,别死了门子。但人情,人情,人有冷暖,情有深浅,不一一描述,就写写三个已故的亲人,在记忆中有着深深的烙记。
1)爷爷的一生辗转
爷爷的身世颠沛流离,很传奇。三代单传:爷爷的爷爷是哥一个;爷爷的父亲本是兄弟两个,弟弟七、八岁时夜里去摘黄瓜,被猍歹咬了命根子死了;曾祖生了爷爷后很早也去世了,家里就剩下爷爷一个,没有一个兄弟姐妹。
十几岁去当了八路,在东北的军队编制里流转奔波,剿胡子。
二十多在一次战斗中,与部队走散被胡子逮到。鞭打侮辱后,绑了双手,套在马脖子上拖行了十几里。据爷爷回忆那时候已经快拖死了,而家族里就这么一个独苗……
在胡子的据点被关在牢里,关了一段时间准备枪毙,胡子的一位夫人看爷爷年轻面目清秀,心生不忍,在夜里送饭时竟偷偷给放了。劫运中遇菩萨,终是命运眷顾!
经此一劫,逃出来的爷爷没有去找部队,怕再次被逮,而是改了名字,走了很远到城市里务工。解放后,寻部队番号未果,此时已经辗转到了阜新,便在煤矿里做了工人。
娶了奶奶,生了几个孩子。生到父亲时赶上六十年代大饥荒、还苏联债,在阜新城里有钱也没粮,只能到城外撸杨树嫩叶子回来混着棒子面吃。
境况日下,孩子中夭折了一个,实在养不活,便携家带口离开了城市,来到了奶奶的娘家---内蒙古农村。村里自己种地,上交国家外会偷偷留些口粮,加上奶奶有几个兄弟,虽然都穷的叮当响,相互照应帮扶,总是能活下去。



爷爷老实本分爱钻研学习,自学成了村子里知名的木匠,在城里还学会了修自行车,当村子里自行车流行时刚好派上用场。就这样边种地边做些零活儿,一家人在村里渐渐站住了脚。后来又生了几个孩子,六个儿子,三个女儿。
到九十年代,本欲回城,去到矿上找时,已是境过人非,老工厂搬迁,老同事寻不见。手上三十年前的工人证,形同废纸。
死心回了村,从此他乡是故乡。
爷爷总是沉默着不说话,在奶奶面前低声下气的。和他在一起的记忆仿佛黑白的、无声的电影片断:他缝补衣服时戴着老花镜,我帮他穿针孔;他站在路旁,目送我回家,我不停地回头看,直到要拐弯时,他远远地站在那里,挥着手。
后来他七十多岁,冬天骑自行车赶集,摔倒在冰雪里,摔断了一条腿和胳膊。自此后便疾病不断,在我十几岁时,结束了漂泊的一生。
2)姥姥是个老干部
姥姥和爷爷两家是邻居,一墙之隔的亲家,但关系似乎并不好。
姥姥家的园子里有颗老杏树,枝繁叶茂,结的杏子肉多核小,特别招孩子。杏树枝叶挨着房檐,房檐上一溜鸽子窝,阳光的午后,杏叶沙沙,鸽子格格地叫。
小时候喜欢往姥姥家跑,即使去奶奶家也会翻墙过去转一圈。奶奶脾气不好,而姥姥对孩子永远笑呵呵的,总会有各种糖果零嘴儿,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她家的里外感觉充满阳光,暖洋洋的,而奶奶家却总是阴着。
姥姥做过村里的妇联主任,是个老党员,那时候的妇联似乎也管着接生和治妇科病。村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大部分都是姥姥接生的。她家有个大大的白搪瓷盆,盆底儿两个红漆字:产盆。
姥姥一生刚强,遇事不求人,而姥爷性格软弱,几杆子打不出声响。家里都是姥姥操持着,拉吧着五、六个孩子。她似乎什么都会做,很多关于吃的记忆都源自于姥姥家,粽子、散状子(小米面做成的糕点)、煎饼、戈豆子(面条状的食品)、年糕豆包……
手上也有无数的针线活计,上学第一个书包是姥姥做的,上有一个五角星和“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至今还记得把它背在身上蹦跳着回家那一路的心情,“我要上学啦!”,恨不得所有的路人都能看到我的书包,永生难忘;从小学到初中的坐垫儿也都出自姥姥的手,上面的花纹刺绣、颜色组合比同学买的成品还要好看……
姥姥家的屋檐灶下,温暖了整个童年。
她活到八十八岁(1927年~2014年),六年前收到病重消息时,我远在南国,从深圳飞回去,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姥姥这一生,经历过数不清的事,但我知道她最大的心病啊,还是舅舅。
3)舅舅,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国字脸,棱角分明,大眼,浓眉密发;一米八的个子,身材健朗匀称,或站或走,总是笔挺着腰杆儿。
舅舅是姥爷家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儿子,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国营林场工作。他是我们孩子心目中的神奇老大哥,让童年的我仰慕不已。
他自制了一台收音机,木制的外壳,自己设计锯出来,上面还有熏烤的花纹;



UfqiLong
他在房后挖了个大坑,做好密封,使用垃圾粪便制造沼气引到厨房做饭;
用电阻丝做了个放双响儿的装置,把炮仗安装好,只要在屋里拉闸就能点燃;
南北营子各家各户的电视机、录音机坏了都会找舅舅修;
村里的广播大喇叭一开始也是立在姥姥家,因为这套音响系统是舅舅搭建的,坏的也只有他能修,村长省心,而舅舅经常用这个喇叭,晨间餐后给全村放流行歌曲;
他养鸽子,房檐下每个鸽子窝儿小巧可爱,也是他亲手制作;
他在夜空下指着织女星、牵牛星,告诉我们隔着多少光年,人类其实是有办法坐飞船过去的,只是他说的方法那时还听不懂;
他在打谷场上教我们倒立行走、打把式,下象棋……
舅舅在我上小学时送给了我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上苏联、南斯拉夫还未解体。我经常把它铺在炕上,趴在黄旧的纸张上,畅游世界列国,废寝忘食。
他有一次到我家注视着地图,“XX,来!考你一下,锡金的首都是哪?”
“甘托克!”
他很欣慰地笑,笑的很开心,嘴里反复重复着“甘托克,甘托克……”
在一个文化蛮荒的村子里,村民手上嘴里都是四时农活,有这样一位年轻的长辈,对于对知识、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影响多么大啊。长大后喜欢看地图,任何地图面前都走不动路,喜欢做科技小实验,喜欢天文地理,往往溯源回去都是始于舅舅。
舅舅在村子里很孤独,常遭人侧目,没有朋友没有酒友,一方面他喜欢的东西、他自我的小世界乡亲们看不上,觉得不务正业,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最主要的:舅舅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据母亲描述,他发病是在大学(大专)里,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住院和在家疗养,反反复复,没怎么上过班。
经常半夜三更,舅妈急促地敲我们家窗户,哭泣着说:“三姐,三姐夫!XX犯病了!”
父亲母亲就会穿衣赶过去,天明方归。
听村里人很邪乎地说,舅舅犯病期间喜欢去村南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土路上徘徊,而那里曾经轧死过一个女人。
严重时,几家就得陪同着出远门,送往外地的医院。姥姥一生不服软,但唯独在舅舅身上抬不起头,操碎了心,被亲人、被街坊邻居埋怨舅舅的病是她宠出来的。
后来舅舅的病愈加严重,导致精神萎靡,体魄下降,最终在三十几岁去世了。留下两个儿子和渐老的姥姥姥爷,白发人送黑发人。
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从未见过舅舅犯病的样子,闭上眼,总是他棱角分明的脸,高高的个儿,笔直的腰杆;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激起我走出村子的欲望,是从小到大的偶像……
想结个尾,说点啥呢……就这样吧,去抽根烟。



🔗 连载目录
🤖 智能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