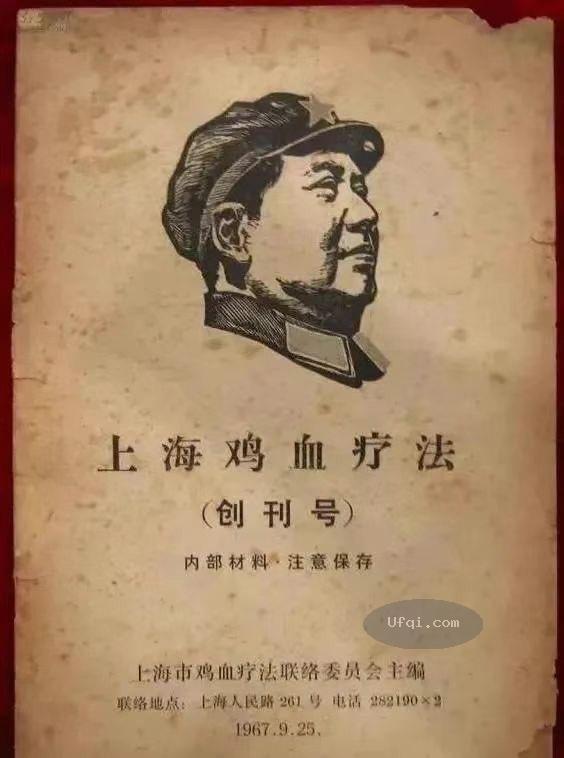2022-04-15 , 3807 , 116 , 169
[编按: 转载于 Beijing Spring/胡平, 什么是胡耀邦的真精神?2005-11-08.]
依我之见,胡耀邦最主要的的功绩是:勇敢地平反冤假错案,组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组织理论务虚会,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保护民主墙,反对逮捕民运人士,保护大学生竞选运动,保护党内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对压制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支持政治改革讨论,抵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这一系列行为中,贯穿始终的有两点:一是对残酷的政治迫害的反感,一是对不同政见和民主运动的容忍。
众所周知,胡耀邦是以 “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迫辞职的。平心而论,这个“罪名”倒幷不冤枉。身为专制政权的掌权者,胡耀邦的伟大之处就在於他拒绝实行政治迫害,坚持对不同政见和民主运动的容忍。
这里,我从自己参加民主运动的经历,谈谈我对胡耀邦的感受。
1979年,我在北京参与了民主墙运动。不久,团中央就主动派人来和我们接触。团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谢昌奎多次和我们诚恳地交谈,明确地表示对民主墙对民间刊物的支持。
魏京生被捕后,谢昌奎向我们瞭解各方面的反应,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他们也是不赞成的。这就进一步拉进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为了保住民间刊物,谢昌奎建议我写一篇论同人刊物的文章,看看是否能以此名义是民间刊物合法化。
在民主墙期间,我们还得到了其他团派机构的支持。《沃土》杂志举行了一场关於社会主义新人的讨论会,中国青年报借给我们开会场地。中国青年杂志曾经约集当时北京地区影响较大的四家民刊《北京之春》、《沃土》、《四五论坛》和《今天》在他们的办公室举行座谈。
尽管在当时胡耀邦早已离开团中央,但是我们都能深刻地感觉到胡耀邦对团中央的巨大影响。来自团派的同情与支持实际上就是来自胡耀邦本人。
1980年北大竞选,当局很重视,至少有三个中央部门派出人员坐镇观察:一个是民政部,一个是国家教委,一个是团中央。其中,团中央派出的负责人是张黎群,张黎群在五十年代出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后因犯右倾错误被贬到四川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写过不少燕山夜话式的杂文,文化革命中自然首当其冲,四人帮垮台后复出。在北京大学的北招待所,张黎群约见我和王军涛等几位主要竞选人,态度相当友好。
不出所料,事后张黎群在向中央彙报时,对北大选举予以高度肯定,和国家教委的报告针锋相对。
竞选活动结束后,北大和人大的几位同学召集各高校的竞选活动的活跃分子在人大校园一间教室开会,总结竞选运动经验。临近尾声,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梁平赶来向我瞭解会议情况,她说耀邦对这个会很关心。原来我们这边的会还没开完,那边中央已经有人要给我们扣上 “开黑会”的帽子了。
幸亏会议有录音,我叫人把一份录音带送交梁平。后来“开黑会”的帽子终於没扣下来。想必是遭到胡耀邦一派的坚决抵制。



1984年,武汉的一些青年理论工作者打算办一份理论刊物。当时,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正以特派员的名义参与湖北地区的整党工作,对此表示支持。多半是由於胡德平的特殊身份,《青年论坛》破土而出,创刊号上发表了胡德平的一篇短文 “为自由鸣炮”。
虽然这篇文章的观点并没有多少新意,但毕竟烘托出一种自由化的气氛。《青年论坛》发表了很多立论大胆,观点尖锐的文章。在1986年夏秋之交,《青年论坛》全文发表了我的“论言论自由”,随后又在北京举行了一场专题讨论会。
1987年1月,当局发起反自由化运动,胡耀邦下台,《青年论坛》也受牵连而被迫停刊。
1986年无疑是中共建政以来最自由化的一年。那时,我应邀在多所高校讲演言论自由,还应邀出席团中央和中宣部举办的政治改革讨论会。记得在团中央举办的讨论会结束后,全体与会者在团中央大楼门前合影,我忍不住对旁边的一位老朋友说: “共产党真是乱了章法,把我辈请到这儿开会来了。”
我自知 “思想反动”,和共产党不是一路。所以我既不打算混入党内,也不指望得到高层领导人的赏识或支持。我对共产党领导人的要求只有一条,那就是容忍。
当时,我对胡耀邦较有好感。我知道胡耀邦是中共领导人中最能容忍的一位。不过,胡耀邦的容忍度到底有多大?他对容忍的理解到底有多深?我仍然不无疑虑。然而我相信,只要眼下的宽松气氛再持续三五年,自由化的势头就真正不可逆转了。
所以在那时,我很担心形势逆转。 十分不幸的是,逆转很快就来了。 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职,随之而来的反自由化运动,使中国的民主进程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胡耀邦存在的重大意义。
十六年后,我从海外媒体上读到胡绩伟的纪念文章,其中引用了胡耀邦在1979年6月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一段讲话,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胡耀邦说: “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
胡耀邦说: “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
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
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至今没有做过检讨。听说他现在还在绝食。
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民心中的烈士。这种烈士是不进八宝山的”。
胡耀邦这段讲话我早在民主墙时期就听说过,但只知其大意,未见其原文。我必须承认,胡耀邦的讲话比我想象得还好。正象林牧先生指出的那样: “胡耀邦当时还只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他不顾党内高层指责他支持民间民主化运动的流言蜚语,在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维护公民权利、维护民主自由和为魏京生等持不同政见者鸣冤叫屈的呐喊,真是惊天动地、大义凛然!
那些至今还在坚持反人权、反民主的立场,继续迫害敢于站起来维护公民权利,推动中国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人们,看到耀邦这一段掷地有声的言论,能不为之汗颜?!还有那些期望过高至今还认为中国没有民主派、体制内更没有民主派,胡耀邦也不过比较开明而已的朋友,看到耀邦这一段言论和他的全部思想、全部实践活动以后,不知能不能改变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
胡适有句名言: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说: “有时候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以为,容忍和自由本来就是一回事,是同一件事物的两面。只不过自由是对自己而言,容忍是对他人而言。诚如殷海光所说: “同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



UfqiLong
民主国家的掌权者,由於其权力受到有效的制衡,想不容忍也难,故而其容忍尚不足为奇。因此,容忍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那些其权力不受制衡的掌权者身上:能够不容忍而却肯容忍才最难能可贵。专制制度是怎样转化为自由民主的?从掌权者的角度,那就是从容忍不同政见开始的。
不错,胡耀邦直到去世前仍然宣称自己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不错,胡耀邦生前似乎幷没有提出过多少政治改革的具体措施。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容忍不同政见,这就是对专制制度的釜底抽薪,这就为自由民主的实现打开了大门。我在《论言论自由》里写道: “当代专制主义与古代专制主义不同,它不是以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恰恰相反,它们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而为了做到和维持这一其赖以生根立命的假像,垄断言论是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阿基里斯的致命处在脚后跟,当代专制主义的致命处在垄断言论。”
一旦有了表达不同政见的自由,共产专制便立刻土崩瓦解。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言论自由呢?我们知道,言论自由属於消极自由或曰否定性自由。只要政府不干涉,言论自由就实现了。我们要求言论自由,无非是说当我们发表各种言论时,政府不要压制,也就是说,政府只要容忍,那就够了。
或许有人会说,有了自由还不等於就有了民主。这话当然不错,不过,共产专制制度不同於传统的专制制度。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例如在传统的君主制下,皇帝是世袭的,文武百官都是由皇帝任命的,统统不需要选举,人民根本没有什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这样的制度下,人民就算有了自由,也还不等於就有了民主。共产制度则不然,共产专制制度包含有若干民主形式。共产制度在理论上肯定了国家的各级权力,包括最高权力,都应该从人民的选举中产生。
共产制度的问题在於,它虽然在名义上肯定了人民享有公共权力,但是由於它 “没有给人民提供一个比投票箱更大的活动空间”(哈贝马斯语),所以窒息了这种公共权力。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就有了比投票箱更大的活动空间,公共权力就被激活了。
简言之,在共产制度下的选举之所以是假的,就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
只要有了言论自由,选举就变成真的了。 这也就意味着,在共产制度下,人民一旦有了自由,也就同时有了民主。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民主墙不曾遭到镇压和取缔,或者是政治改革讨论热潮不曾被强行中断,或者是反自由化运动被有效地制止,今天的中国将会是什么局面?
由此,我们才能深切地理解胡耀邦的容忍具有何等伟大的意义。
容忍——这就是真正的胡耀邦精神。



🔗 连载目录
🤖 智能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