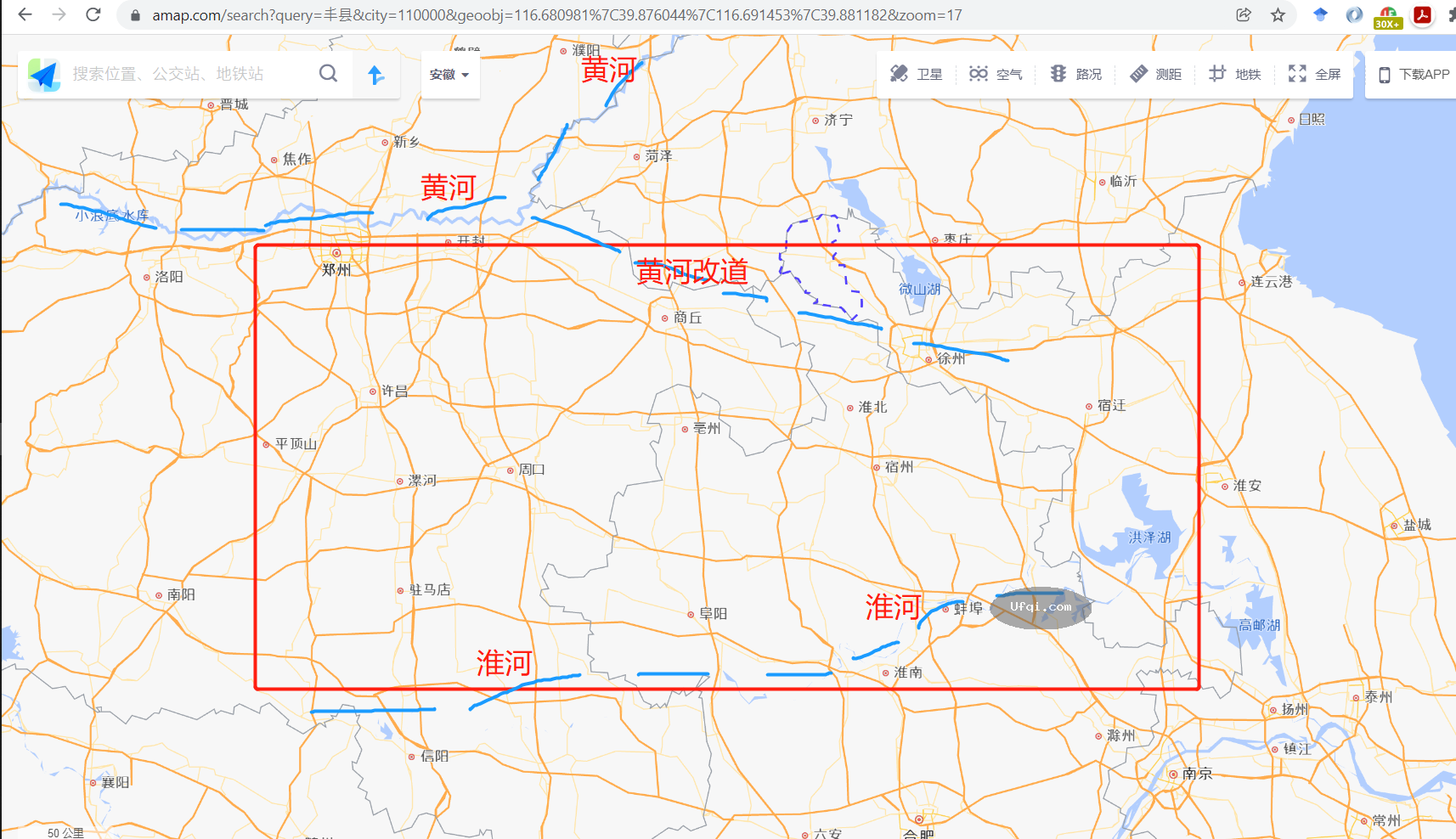2024-09-21 , 12083 , 2422 , 130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13: 反右以后莫发言-3
我们的家庭生活平静而充满了温馨。
尽管母亲对父亲有意见,但很少跟他吵架,即使吵架也不当着我们的面。父亲非常疼爱我们,虽然我们三岁后就很少用搂抱、亲吻来表达父爱了。
对弟弟们,他让他们搭马马肩(骑在他肩上),有时拍拍他们的肩膀,或摸摸头。但对女儿们就没有这些举止,很有点授受不亲的味道。他在进我和姐姐的房间时,总要敲门征得我们同意。
我母亲也不常抱我们、亲吻我们。 这是因为她得遵守另一套不成文的规矩:共产党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在五○年代早期,共产党员除了吃饭睡觉外,每一分钟都属于革命,都得花在工作上。



抱孩子与革命无关,得尽快做完了事,否则会挨批,说你不全心全意为革命工作。 起初,我母亲很恋家,所以不断受到批评,说她家庭观念重,后来她才慢慢习惯了永无休止的工作。当她每天夜里回家时,孩子们早已入睡,她就坐在我们床边看着我们熟睡的脸,听我们平静均匀的呼吸,这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她一有空就搂着我们,轻轻地给我们搔痒,尤其是搔胳膊肘,简直舒服透了。我最喜欢的还是掏耳朵:搬张小凳坐在她面前,把头枕在她膝盖上,眯着眼,好像飘上了九重天。掏耳朵是一种享受,我记得小时候常看见那些职业掏耳朵的人担个小担子游街窜巷,一边是竹椅,另一边挂着一串串晃来荡去的五花八门掏耳工具,小勾匙啦,带绒毛的小棍啦,等等。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干部们星期日可以休息了。
我父母爱带我们上公园,去儿童乐园玩。我们在那里荡秋千,坐旋转木马,还沿着青草覆盖的斜坡往下飞跑。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曾翻着筋头从坡上滚下来,我料想会落在我父母张开迎接的胳膊里,结果却撞到几棵芙蓉树干上。 但父母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仍是不多。姥姥总摇着头叹息:谁见过这样当爸爸妈妈的?
她于是把全部心血都花在我们身上。 但她怎么也照料不过来我们这四个小家伙,我母亲就从宜宾把俊英娘娘请来帮忙。她和姥姥处得十分融洽。到了一九五七年初,母亲又请来一位保姆,住在我们家,她们三人也和睦无比。也正在这时,我们搬进了新房子,这是以前一个基督教教士的住宅。我父亲也搬来了,第一次我们整个家庭都生活在一起了。
新来的保姆十八岁。她第一次到我们家时,身穿印花的大红大绿棉衣裤,这在城里姑娘看来是土气十足。当时城市居民流行穿的衣服是素色,这是共产党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潮流,城市妇女服装式样也学苏联。
而我们的新保姆穿的是传统农民服装开襟式,布做的钮扣,而非新式的塑料钮扣,不用皮带系裤子,而用松紧带。许多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姑娘都马上换衣着打扮,以免被人当乡下佬。但我们的新保姆则安然自得,显示她极有自信。
她的手大、粗糙、黑里透红的面颊上,挂着略带羞涩憨厚的笑容,一笑总有两个酒窝。家里人很快就都喜欢上她了。她和我们一道吃饭,和我姥姥、俊英娘娘一道做家事。
姥姥很高兴有了两个知心女友,因为我母亲从没时间在家里陪她说话。 新保姆来自地主家庭。她拼死拼活要离开农村,离开那个受歧视的天地。
一九五五年肃反结束后,政治气氛相对松弛了,又可以雇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了,我家才敢雇她。共产党建立了一套户口制度,每个人都得在她们生活的地方注册,只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才有食物配给。新保姆是农村户口,所以她在我家没有粮食供应。
但我家里的配给足够供她吃。 一年后,我母亲帮她把户口从农村迁到成都市。 我家还付给她工资。政府的供给制已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取消。我父亲的警卫员也取消了,几个副部长合用一个勤务员,在办公室为他做打开水、安排汽车之类杂务。我父亲现在按他们的级别拿固定工资,我母亲十七级,我父亲十级,他的工资比她多一倍。



UfqiLong
当时物价很低,又不是消费社会,因而两人工资加起来绰绰有余。
我父亲算高干,这是由十三级以上干部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在四川省有几百名,十级以上干部约有几十名,而四川省当时有七千二百万人口。
(未完待续, To be contd)



🔗 连载目录
🤖 智能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