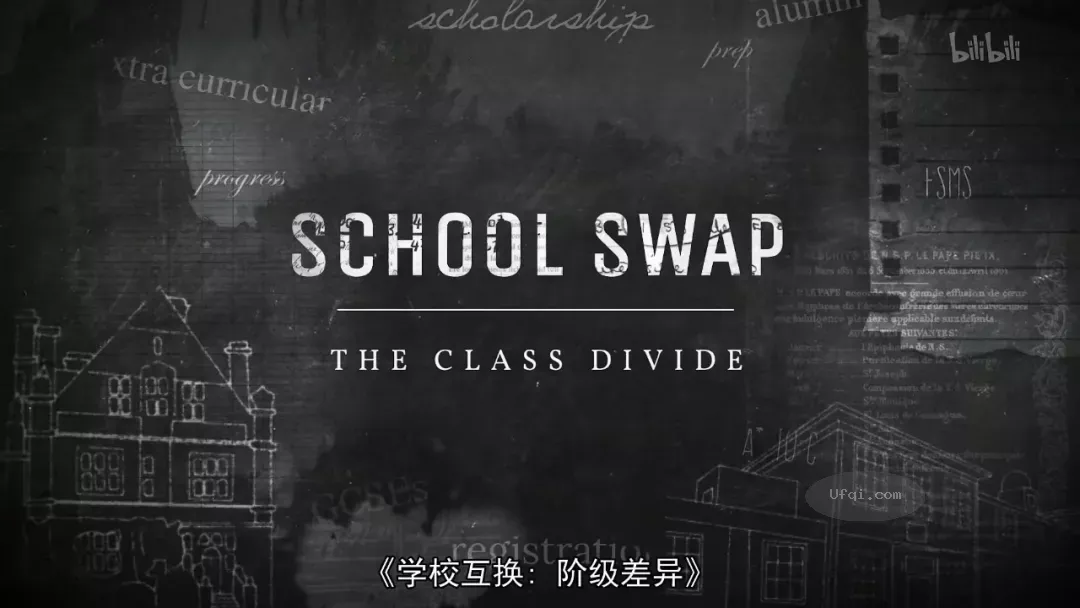2021-02-15 , 2008 , 104 , 166
三 “真的害怕”
有老人承认自己投资养老院是为了合同上许诺的“福利”——18%、12%、10%的回报听上去总比银行存款利息要诱人。但更多的老人是实实在在奔着养老院床位去的。
高焕英说,衡福海养老院暴雷立案后,警方来找受害者调查。调查表上写的是“投资人”,她不同意自己是投资人,“我们明明是为了预定床位”。她要求改一下头衔,起初没有得到同意。
后来,表格上被不满的受害者印上一句话:“受害投资人登记表”,针对的是有头脑的消息灵通的年轻人,而我们这两千名老年人,我们的养老金连放银行都觉得不保险,又怎么会去投资呢?
年龄越长,死亡的终局逐渐逼近。老人们偷偷为自己规划了最后一站,许多人报名养老院时隐瞒了朋友、儿女甚至是伴侣。
老人詹荷花说,养老不可能靠子女,“没有必要告诉他们,自己掏钱,自己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希望不要增加他们的负担,不是更好吗?”
高焕英把钱存到养老院时也没敢告诉儿子,怕儿子儿媳有想法,有钱不给他们。她很少和儿子讨论养老问题。直到养老院暴雷后,她去维权,儿子知道后,埋怨她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为什么一直瞒着他们、不相信他们。“
有时候只能背着他们,自己暗自流泪。原来是想自己早一点做安排,早一点做准备,没想到这么一个下场。”
她没办法向儿子讲述自己更深层的恐惧与不安。现在,高焕英住在儿子家,给儿子带孙女。儿子女儿孙女睡主卧,她和老伴睡次卧,她89岁的妈妈睡最小的房间。
妈妈的卧室摆了一个塑胶式便携式马桶,前阵子刚刚在聚划算上买的。她每天清洗马桶、喷消毒液。现在妈妈上厕所需要她来脱裤子,擦屁股,妈妈已经分不清楚大便和小便了,有时候大便完以为是小便,裤子匆匆忙忙拉起来,粪便沾得到处都是。
她偶尔忍不住也会凶妈妈,“你大便就说一声啊!”
但妈妈还是弄不清楚。现在每天晚上凌晨两点,她都要定时喊妈妈起来上厕所,怕妈妈拉在床上。
高焕英戴着一副厚厚的框架眼镜,穿着一件土黄色袄子,黑色健身裤,她笑着说这是“工作服”,正准备为家里做新年大扫除——即使她已经到了扫会儿地就会腰痛的年纪,她仍然朴素、兢兢业业地履行着母职的每一项任务。
高焕英老实讲,她并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以后能帮忙养老,儿媳总是隔了一层,现在洗碗、洗衣服、做饭,儿媳觉得高焕英来做是理所当然,“我们在家里说话都很小心的,不能大声说。”
她说起自己的妈妈,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四个人轮流给妈妈养老。前几年,每当轮到弟弟时,那三个月弟媳就把妈妈偷偷移到养老院去养。那家养老院条件很差。
后来因为妈妈的房子拆迁,拆迁款分成了五份,多的一份给了弟弟的孩子。弟媳这才转变了态度,愿意在家里照顾妈妈了。
高焕英还提起自己的一个朋友,独居,有一阵子痴迷保健品,生病了以后药也不吃。后来儿媳发现她死在沙发上,电视还开着,一只鞋子掉在地上,旁边还有一滩血。没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儿媳打开柜子,发现里面装满了瓶瓶罐罐、保健枕、保健衣。
“真的害怕。” 高焕英说。



她更担心自己的小妹妹——就是那位和衡福海老板打架的孤寡老人。妹妹胆子小,不敢见记者,她在电话里说,“我已经被骗了,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妹妹还和高焕英说过,自己哪天就要死到衡福海养老院去。
而桃江的丁丽华则是瞒着丈夫、女儿报了养老院。话说到一半,木门推开——她的丈夫回来了。丁丽华赶紧说,来客了,这是医院来做调查的人,来了解术后恢复情况。老头信以为真,便开始说为了给她做血管瘤手术,现在还欠了七八万没还。现在他每天出去做电工,修水管,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赚上个两百元,慢慢还债。
丁丽华的女儿反复强调自己“嫁得近”,她难过于自己家只和妈妈家相隔一条桥,骑电动车五分钟就可以到妈妈家,却没想到妈妈还是瞒着所有人报了养老院。
她从没想过这回事,觉得自己可以把妈妈照顾的很好,每周都会准备好蔬菜给妈妈送过去(她在做社区团购),妈妈手术时也是她在照顾。
可妈妈直到第二次去做手术,以为自己就要挺不过去时,才将养老院暴雷的事告诉了她。女儿搞不懂丁丽华怎么想的。
“哪个儿女听了不会伤心呢?”她没敢在妈妈面前说这话。
在这之前,丁丽华带着女儿和我去都好养老院转了转。在离曾家坪半小时车程的县城郊区,都好养老院仍然还在运转。黑夜中,一栋和县城环境格格不入的、崭新的楼盘伫立着,窗口里散射出明亮、温暖的灯光,三个红色的大字立在楼顶,“光荣院”,前面是一家配套的“养老服务医院”。
后头养老,前面医疗,这是丁丽华在农村里难以见到的场景。
丁丽华边走边说,这里条件真的很好。她交的五万元是入住这家养老院的门槛费,预定的是相对便宜的双人间。
可现在,如果想要入住这家养老院,她还需按照非会员的价格另外交钱,交的本金再也不算数了。丁丽华怎么也没有想明白,她为什么不再能入住这家美好、干净、舒适的养老院了。
(夜晚中的桃江都好养老院)
四 离开的业务员,还在运转的养老院
暴雷后的好几个月,衡福海的业务员吴秀芳都没再找工作,觉得自己“被它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去年八月底,警察打电话给她,让她退还在衡福海工作期间的所有工资。她感到委屈,自己又没有拿老人的钱。
并且,保底工资就一千来块,业绩提成在很大程度上与支出挂钩,要多跑客户,时不时到老人家拎点水果看望,赚的钱还要付房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存。
她东拼西凑,凑了一二十万出来。后来她还是留了案底。
她今年40岁,上学出来就在外地打工。2017年她加入衡福海,希望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离家近一点,“反正那里面什么证件都齐全,我们都是农村的,也不知道这一些”。
吴秀芳自认没干什么亏心事。培训的时候,老板要求她们去发传单,把政府发下来的证件给他们看,“说这个老年公寓,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都是很吃香的,叫我们好好干。”
她声称自己只给老人们发过传单,全凭老人自愿。至于外界所传的业务员给老人洗脚,吴秀芳说,“这么低三下四的没有做过,都是光明正大的。”
(2020年)去年3月,上班时老板给业务员开会,总共来了零零散散三四个人,说受疫情影响,钱周转不来,取钱要推迟一两个月。同样受疫情影响,越是有疫情,客户越要拿出去。慢慢地老板又说要推迟三个月,时间不断延长。



UfqiLong
到最后,老板就被抓走了。她的姐姐跟着投了十万元,没拿出来。嫂子运气好,去年4月把钱取出来了。
吴秀芳上个月重新找了份工作,在桃江县卖商铺。她上着上着就开始想:这也是拿业绩的,万一房子出了什么问题,我会不会又被找?她去找老板辞职,理由是,“万一你们这个是假的,我负不起责任”。
对方说,“怎么可能?我们的证件这么齐全”。
她心想,以前在衡福海,还不是证件那么齐全,老板说得那么肯定?
(衡福海养老院仍在运转中)
位于市中心的衡福海养老院还在正常运转,还有八十多个老人居住于此。走入房间,设施的确如老人所说“能匹配三四星级酒店的水平”:木地板,胡桃木床,地暖持续散发着热气。
几位老人在热热闹闹地打麻将。只是街边那间墙上写着“替中华儿女行孝”的老年服务中心,已经关上了大门。
曹迎林生前投资纳诺养老的办公室藏在一条破破烂烂的小巷子里。门口的招牌是一块磨损严重纸板,上面画着一扇金灿灿的拱形门,“纳诺老年公寓欢迎您”。楼下的水果店老板没好气地说,哪有什么养老院,老板都跑路啦。
五 “这是我”
在江边为跳江的老人打鼓招魂三天后,张志成患上了风寒,咳嗽、嗓音嘶哑。敲鼓是他唯一的爱好,也是他所有的生活。江边的环卫工人都听说过他,知道他今年60岁,无父、无母、无子女。因为小时候的一场高烧,他有智力残疾,“相当于8、9岁小孩的样子。”
在江边一家名为“阿里郎”的 KTV 里,我见到了张志成和他的妹妹。妹妹张好听朋友说,哥哥上新闻头条了。等回到 KTV,她问哥哥,你为什么要敲鼓。
哥哥说,他要把老人“敲起来”,还说那些害老人的人都该死。但至于更多的——比如出名这件事,哥哥就并不是很明白。只是在妹妹指着视频上的截图,问他这是谁时,哥哥知道点点头,“这是我。”
(正在打鼓的张志成)
张好今年56岁了。自从丈夫死掉后,她再也没有结婚——现在哥哥住在她家,每天早上,哥哥跟着她后面来上班,吃住都由她管。拖着哥哥,哪儿有人会愿意和她结婚呢?
张志成被认定为残疾三级,每月补贴400元,妹妹说,这连早餐都不够吃。可她也不忍心放哥哥去福利院“等死”。
下午四点,张志成从午觉中醒来。等他走下楼来,张好把他的外套羽绒服拉开,仔细替他围好围巾。张志成不高,一米五的个头,戴着一顶帽子,睫毛长长的,乖巧地让妹妹摆弄着。
他的休息室里堆放着大鼓、小鼓、锣鼓、大钹。为曹迎林打鼓时,张志成拿上了最新的一面鼓。那是妹妹送给他的六十岁生日礼物。
张志成再次敲起鼓来,没有节奏地点点鼓面。门口拴着的一条黑狗被鼓声闹醒。黑狗叫贝贝,原来在江边流浪,半年前,张好将它收养了下来。
现在,哥哥的朋友除了那些鼓,就只有这条狗了。如果再老一些,哥哥和自己的养老怎么办?她也没有答案。
(文中除曹迎林、张志成、刘一木、唐朝外,其他人物为化名。)



🔗 连载目录
🤖 智能推荐